2023年9月,修完我的第三个硕士学位,人生进入了新阶段,再次去成为一个新社会的移民。十年前,我在香港做过一次这件事,如今再做一遍。
过去一周,我重读了过去一年主要发在豆瓣平台上的帖子。
其中有大约半年时间,我没办法在除微信朋友圈的任何国内平台上说话,所以那是空白的赛博简中半年。空白本身也是一种赛博表达。我没有说出的话,已被规模化的空白展示出来。
至于那些我能说出来的时刻,我在那些帖子里,看到自己的努力撑住、和无可回避的痛。
在这个公众号停止更新的漫长周期里,我的手机还时不时收到来自官方提醒,某某陈年旧文又没了。
在翻阅还剩下的那些文章时,我多少有些汗颜曾经的那些少年意气,但也能感到那种短暂的青春与美丽。我不会装作我还能回到从前,因为这些年的辛苦、创痛和抗争,在我身上有足够深刻的烙印。也有没变的。那是我性格里那些——暴烈的,飘忽的,伤心的,淡漠的,决绝的——的部分。
我会从去年9月,我刚到捷克的那个下午开始整理我的“近况”和“远况”,做一个移民知识分子的社交文本细读。更系统的写作,我会写在给三明治的专栏里。
2022.9.17
(刚到捷克,收拾一天,到下午)
不知怎么就睡着了,梦到一片虚无之境,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念,「白云千载空悠悠」,觉得这一句中文实在太美了,然后我醒了过来。
2022.9.23 标记图书★★★★☆ Lost in Translation: A Life in a New Language
自行翻译的一段: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Extreme mobility)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我在给三明治的文章《出走欧洲这一年》的最后,翻译过这一段。)
标记图书★★★☆☆ 《重访东欧》
读这本书的旅程,我和霍夫曼访问波兰的路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让我自嘲一下就是,我一路上找普通人聊天,已经困难重重。霍夫曼回归波兰后,全是谈笑皆鸿儒。而我一直在刻入骨髓的孤独中。
(我的豆瓣账号被封禁半年,微博被「无限期」封禁。过去半年后。)
2023.4.13
180天,我出来了。
2023.4.13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
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有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 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Primo Levi
2023.4.26
(我先是贴了一张2021年最后在深圳的那段时间,徘徊犹豫是否应该离开时,所写的段落:)
(两年后,我经历完德国、波兰和捷克的学习和生活,再次回到德国哥廷根。我写道:)
在德国、波兰、捷克绕了两年,我现在回到德国,并且现在就在语言班。我和一个日本人、一个乌克兰人、一个印度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起学德语,除了我,她们四位都是女性。日本人曾在东京做「会社员」,男朋友三年前来慕尼黑工作,现在到哥廷根读书,我们周末在汉诺威的火车上偶遇了,男友长得像年轻小栗旬。她辞职,申请Working holiday来了这里,开始学德语。我也不意外,日本护照是全世界最有特权的护照。
乌克兰人是个数学家,战前就来了哥廷根,在大学研究所工作,她说自己既要学英语,也要学德语。她知道所有名词的前面该用der,die还是das,这天赋让人惊叹。我问她是否是因为乌克兰语的名词词性和德语基本一致。她用口音铿锵婉转的英语告诉我,我们乌克兰语讲起来根本不说这个。那我想这就是数学家善于归类的纯天赋了吧。
印度人来自孟买,她丈夫来自德里,在德国工作两年了,她们在印度几年前结了婚,现在她来了刚两个月,她不是穆斯林,很世俗,骑个自行车迅即如飞,英语讲得很好。现在她要做的是在德国找一份工作。哥廷根尽管是学术城市,但要找一份研究以外的职业,德语才是更重要的。
巴基斯坦女人比较有趣,她是穆斯林,Hijab裹得很紧,第一天上课甚至是丈夫送来的。但她上课很积极,经常抢答,我们练习对话时,她反应也很快。在我们试着说我们所知的从A到Z的德语词汇时,她知道一切关于超市、食物和日用品的单词。在讲到职业时,她说自己是Hausfrau,这就难怪了。
我则多少有些不接地气,讲到职业,磕磕绊绊说出Schriftsteller这样的词汇。老师说,你能不能说一些正常的职业。而且你如果是记者和编辑,就不要说自己是作家,作家是写书的。我用德语缓缓回复说,我以前的职业是记者和编辑,现在我就是Schriftsteller。
我们都在如幼童般学一门语言,但我们又都在各种场合自学过这门语言了,于是我们都掌握了庞大地图中的小小一隅。而那一隅,多半都关乎我们已经走过的漫长岁月,我的词汇库里是那些老师口里不正常的职业和名词,巴基斯坦女人的词汇库里是超市里所有的蔬菜、肉类、水果和洗衣粉。
我于是搜出这条两年前的想象自己在语言班的内容。我现在没有丝毫难民感——事实上,这两年我交往了好些曾是难民(如今获得公民权)的朋友,他们都太厉害,太激励我了。
对了,当我在说她们英语好的时候,并不是说她们有一口伦敦腔/美国腔。我觉得我英语也不错,但是我是一个非英文母语者在使用这门语言。这曾是一门殖民的语言,那既然如今,全世界都在使用它,那它就得有新的后殖民传统。They write you, you write back.
2018年时我在香港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过去两年我在德国、波兰和捷克都必修或旁听了好些后殖民主义英语写作课程,一口正宗xx腔,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我要做的事,就是write back。
现在德语关乎我的生存,虽然很烧脑,但在波兰学了一点波兰语之后,我觉得德语至少看着很亲切。
我想说做一个移民/难民,一定意味着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阿伦特说的。你有强大的自信,相信将自己连根拔起后,仍然能在俗世追求一场比你所拥有的,要更幸福的生活。我并非重新开始,而是一切我曾经的自我选择,促成我更多的自我选择。
我也不用去羡慕这条帖子里的朋友了,因为显然,我相信自己有更深思熟虑的强大生命力。
2023.4.29
明天就要去巴尔干了,赴2019年说好的约。
2023.5.13
最近这几个月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
终于在我国大流行结束后去换了回乡证,整整十年前去到的港村,算是彻底告一段落。
在德国,忍着极大的尴尬,使用谷歌实时翻译,把完全听不懂的Erste Hilfe Kurs(first aid course)上完了,7个小时,拿到证书,因为这是拿德国驾照的必经之路。
每天的德语课程。联系柏林的房产中介。做田野,读文献,写论文,完成我的第三个硕士学位(最初我觉得挺丢人的,现在觉得还挺吊的,因为每个学位都彻底改变了我的能力,和命运……)。还有关于出版的那些东西。还有之后在异国的居留权。
德国白人朋友说我这是Shenzhen speed,因为他2019年和前女友一起去过一趟深圳,爬上了平安大厦顶层,感叹这句Time is money, efficiency is life的口号既神奇又疯狂。他让我慢一点,要享受生活。但其实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这边的移民朋友们,孟加拉人和印尼人,甚至比我更快,更不享受生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挺住就是一切。
其次就是我早就习惯了这种挣扎着追寻自由的生活,因为那足够自我,足够“海拉鲁”,足够改写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那天要写到“海拉鲁”,因为我好像刚买了游戏《王国之泪》预售版,但我从来没有打完过塞尔达传说的任何一部游戏。最多的时候,我的林克有滑翔伞,可以飞出村庄。)
2023.5.16
(这天为什么会引用以下这一段书里的内容?好像是脱口秀行业覆灭的那天吧。)
「德国在 1934 年至 1938 年间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风景图册、大自然抒情作品,以及许多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除了刻板的纳粹宣传文学之外,德国能够获准发行的书籍几乎完全来自那些范畴。大约从两年前开始,这个趋势就已经不断退潮。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不管再怎么挖空心思,也越来越无法营造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氛围。
不过,在此之前的状况只能令人摇头叹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和雏菊花、稚子放长假时的欢乐、初恋时光、童话情景、烤苹果和圣诞树。这种文学充满了赤子之心和缺乏时代背景的色彩,仿佛有约在先一般,在游行队伍、集中营、军火工厂和“冲锋队”募捐铁罐的环绕之下纷纷出炉。
如果有谁曾经像本书作者一样,于偶然之下必须大量阅读此类书籍的话,便会逐渐发现,它们在乖巧、平静和温柔的叙述背后,正在字里行间不断发出呐喊:“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不受时间影响,回归于内心世界了吗?你难道没注意到,并没有任何事情对我们造成伤害吗?你难道没注意到,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吗?请记住这一点,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我们向你提出恳求!”
我认识那些作家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每一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令他们无法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方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人被逮捕,要不然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童年时代的回忆已无法再提供保护伞。不少人因之而崩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将来我会找时间叙述其中的一些故事。
以上就是德国人在 1933 年夏天所面对的矛盾。那看起来就仿佛是,必须从几种让心灵死亡的不同方式之中作出选择。我们可以说,于正常环境下过惯日子的人,在这里会感觉自己若非进了疯人院,就是待在一所精神病研究所里面。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无力回天。此外,那个时候还算是比较无害的阶段,接着还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我想躲在私人领域里面,在一个有遮蔽的小角落安身立命之尝试,很快便一败涂地。其中的原因是: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狂风暴雨从四面八方侵袭我“私底下”的生活,马上把它吹得四分五裂。比方说,一个可称得上是我“朋友圈子”的小团体,就在 1933 年秋天消失得不知去向。」 ——《哈夫纳回忆录: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2023.5.25 Moving to a new country and adapting to it can destroy relationships.
(这是我的俄罗斯学姐的毕业论文里的一句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她决定写这个题目,前苏联移民女性在瑞典如何生存。她写民族志。这一句是她采访的在瑞典的前苏联女性——一个非俄罗斯人用俄语的回忆。最初搬到瑞典来时,她们是夫妻两个人,树年后,她和丈夫离婚了。我的俄罗斯学姐问她为什么,以上是她的回答,从俄语翻译成英语。)
2023.6.7
油管最近不知为何开始给我推432Hz的纯声音,说会释放潜意识的不良能量。有天夜里我醒来,打开这个声音,似音乐非音乐,然后香甜地接着入睡了。我只记得身处一片云雾之中,有许多人来来去去,我开始不知为何感到委屈,感到悲伤,然后哭了起来,半梦半醒地哭,这场梦中的哭泣,就好像一片叶子,在水里,不知道为什么,荡来荡去。
2023.6.16
(我为毕业论文,在柏林做田野期间,顺便去看了一些柏林的老房子,为未来搬过去做打算。)
在柏林Neukölln ,带着懂房地产的朋友,看了两套房,算是练练手。看完有点郁闷。她安慰说,第一次看房就买房,就跟和初恋结婚一样不现实。我一下释怀了。
2023.7.4
大概是十几年前有一帮人做独立校园媒体,毕业前引用了《一代宗师》里那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觉得很酷,有种善恶终有报的爽感。然后去了香港,至此走上不归路。做的大多数自认为有社会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新闻报道、采访研究还是社会抗争,都没有回响,一丝一毫也没有,然后一身折磨,满心创伤,活在惩罚、监控和噩梦之中。
再在国门完全封闭的两年多前到欧洲,感慨过去十来年,一遍又一遍地重新锻造自己,又时常会想起二十来岁写的看上去意气风发的“人生是一场出埃及记”,但真的出埃及可没有分开红海的壮阔,也不会期待什么回响,习惯在全新的孤独中去打造微小的共同体,一心只想去过那种权力不希望你过的生活。
上个月Mubi推荐的每日电影恰好是《一代宗师》,鬼使神差打开了。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打开投影,看了一个下午。才想起原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前面还有八个字,那不太起眼、也不太被十几年前的心绪记住的八个字。因为那八个字完全没有目的,不求回报,不期待回响:
凭一口气,点一盏灯。
2023.7.30
告一段落
欧陆对硕士的学术要求还是很高的。
回忆起来,我刚到这个德国城市的那半年修了五门课,每门课的term paper都需要15-20页,不包括bibliography。波兰和捷克的两个学校要求比哥廷根要低一些,但低不了太多。这次的毕业论文thesis是30000个单词。
我第一个硕士在港大新闻系,毕业是写一篇3000-5000单词的英文深度报道。第二个硕士在港大文学院读英文研究(文学track),毕业论文是写一篇5000字左右的capstone project(比较奇怪学院不说这是thesis)。
当年读的时候,两个都很吃力,第一个是全职读,第二个是边打工边读。除了当时能力差劲以外,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很短,没法充分地浸润其中。比如在新闻系,刚刚适应英文上课,就要开始找冬天的实习。在写毕业报道的时候,还要想着如何留在香港找一份新闻的工作。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到12个月里。
文学系好一些,课程设置非常非常先锋,后殖民主义文学尤其好。但是因为香港高校效仿英国的教育产业,把MA和Mphil分开,所以MA仍然缺少足够的时间去消化那些学到和读到的东西。我当时一边在厂里打工,一边打官司,一边读这个专业,很吃力。所以我把当时的所有资料打印出来,直接带到了德国来,时不时复习一番。
欧陆这两年的训练和浸润其中,是我体验最好的一次,从理论、方法论到真正做田野、做研究,我都有足够的时间和不同的导师、或不是导师的教授们,不断地交流。
我自己觉得,一是我的英文能力、各方面的生存能力有了一个质变般地提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第二个硕士,作为一个移民,我提前接受了后殖民教育。
二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真的离香港那种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比较遥远。在这种地方,小城市尤其更便宜。我不会整天被铺天盖地的金融、财富、房租的压力弄到去被迫学习那些新自由主义技能,比如在地铁口和证券经纪人去开证券户口这种很傻缺、但又很香港的真实故事。
我现在找到了我为何要读三个硕士的理由:
第一个是因为我不想在国内做新闻记者。
第二个是因为想为润提前做语言和思想的准备。
第三个是因为要执行离开,当然离开只是手段,我是为了恢复公共写作。
现在执行完了。读不读博士,也许现在多了一点点信心,但是有什么研究课题,得花五年时间去做的?得再想想。
生存和身份永远是第一要义。简单说,交税是第一要义,有德国学位+两年交税,可以申请永居。
其次,即便是在德国,你还是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环境中的移民。
前些天数了一下过去十年做的五份工作。两份记者编辑YZZK。DUAN。都在香港,自由媒体。一份风投机构FENGRUIZIBEN。一份学术机构GANGDAZHENGZHIXUEXI。一个厂工GUANGDONGOUBOKEJI。我没任何成为领导的职业规划,唯一的规划就是要自由地活。记者不让做了,可以去为挣钱而吃屎一段时间。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生活很简单,明确目标,面对无处不在的突发情况,保持淡定,一步步执行,一步步润。不和权力媾和与妥协。
2023.7.31 电影《晨光正好》 ★★★★☆
"I have forgotten how."真像我的异国生活。我突然意识到,移民生活至少在某些时空下,也是一种丧偶体验。
2023.08.04
成为散居者/离散者/移民,成为一个国家的少数族裔,成为第一代移民,是否还使用母语写作,如何使用第二或三门语言,如何准备好所有的资料去外国人办公室,如何让银行卡里有官员们认可的金额,什么情况可以办公立医疗保险,什么情况可以申请何种居留,你在何种程度介入母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你要如何努力不让自己在接收国社会彻底缺席,你应该如何进行跨国的公共参与,你要如何面对一个自由民主体制的系统性不公,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需要第一代移民去面对、行动甚至抗争的……
如果我做移民生意,我会首先教中产白领多读读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国内语境下,老被我国新左派奇形种们,拿来证明对抗西方的重要性,这当然是一种脱离语境的逆练。
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自由右派中产阶级,如果对后殖民毫无了解,在移民后很容易陷入失语,因为作为移民你一定会遭遇一种系统性的歧视性环境,尤其拿着一本我国护照的时候。但你此刻陷入一种极端的交叉性之中,面对很多问题,脱离语境,你往往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痛苦。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呢?我批评它难道不是跟小粉红一样了吗?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不是的,是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问题。
2023.08.28 电影《过往人生》 ★★★★☆
移民的类型真多啊。而我呢?二十二岁时以为到香港,就到此为止。三十岁又来一次。在大流行大封锁期间。诀别爱人,不断地诀别爱人。不是同样的人生境遇,没有一起出走,被打断的团聚,渴望,恨,痛,无可奈何,任它去罢。走到的竟然还不是英语国家。牙牙学语。我的梦里不是中文,我的梦没有声音。对她说理解她的选择。对她说我没有回头路。那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呢?Nora想拿的那些奖,我不想,我只好奇我能活到哪一岁。
2023.09.05
在德国的工作快有眉目了,不过话别说太死,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故。看看去努力做连接者,会是什么样。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真的能帮到人。不坐班,但得住柏林。有时间写我那本拖欠的稿,有时间上德语课,有时间自我寻找较长时间的项目,一个个默默做下去,找到一种可以不损害个人福祉、有未来可持续、而不是为爱发电、充满日常威胁的生活和贡献方式。这是我十年前,刚做港媒记者时,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模式。
过去十年,我在香港或深圳或北京,始终找不到这样的模式。我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的边缘人。但过去十年的五份工作和三个硕士,给了我一身新自由主义跨国技能,这是特权。我想许多人身上都有自己各自的 Privilege 和 Marginality,重要的是认识和理解到这些,知道自己的身体处于社会结构的哪个位置,然后去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当然,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辛苦,这同样是过去十年的经历教给我的。你得理解,无论在哪里,你仍然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
自然少不了那无穷无尽的歧视性的许可文件之路。这条路我曾走过一次,走了七年。移民的世界充满了如下词汇:技能、语言、入境处、墙、种族、性别、阶级、外国人管理局、劳动部、国籍法…这些词汇把你锻造成流亡高手、官方信件收发室、自我观察大师、努力支楞职业演员、被迫多语言使用者。(斜体字抄袭了Dubravka Ugresic的小说《平衡的艺术》,出自《狐狸》一书)
2023.09.14
今年二月,时隔两年回国,要办因为封锁而拖了好几年的回乡证,去老家县派出所注销户口。那段时间死人比较多,家对面的县人民医院每天都死几十个人。很多年轻人来派出所帮家里其他亡故亲人注销户口。
我没多想,径直问派出所裹着很厚深蓝色棉袄的大姐:我来注销我的户口。
大姐看着我直勾勾地说:你的死亡证明在哪里?
她说完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竟然有几秒钟,她没觉得尴尬,我没觉得冒犯。我们只是沉默看着对方。此后我反复想起那个沉默的悲伤情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失去了谁,但她看向我如看穿一个莫名其妙的鬼魂。
她在那一刻只是个照章办事的小吏吗,还是她一瞬间妄想了和鬼魂说话的可能吗?
2023.09.18
关于这天与去年,我记得许多许多的痛。
2023.10.11
夏天结束,人生悲伤事情真多。
2023.10.20
重新过上坐公共交通上下班的日子。但纯粹就是坐地铁,谈不上挤地铁。给外管局发去了我的工作合同。吃午饭时把她送的手套忘了,现在去找。再独自去看《花月杀手》,迟到了二十分钟,结果还在放广告。
2023.10.23
今天去柏林出差,顺便又看了一次房子,再次失望了。
位置特别好,Kreuzbergstraße,房子装修得特别好,暖气非常现代化,电表是全新的,马桶不是坐地的而是入墙的,看这些是上次看房学到的经验,朝向虽然朝北但这不算啥了。之所以降价20%,是因为之前楼上属于一个房屋建造公司,疫情前在加盖一层,然后疫情期间,房屋建造公司倒闭了,于是外立面和院子里的脚手架,就这么一直绑在外面。
整栋楼院就这么像木乃伊一样被绑了一年多了,新来的物业管理公司联系不到原来的房屋公司负责人,也不知道何时脚手架会解除。
对了,这栋公寓楼的建成日期是1900年。建造日期早不一定差,因为那时候建造的房子墙体厚,用料扎实,隔音好,保暖好。比起1945年以后那几年修的房子反而更好。
但是1900这个年份还是让我太惊讶了,那是欧洲的大国协同的长和平时代,是两次大战以前的长19世纪,是民族独立蠢蠢欲动的时代,是帝国殖民的晚期,是黑暗之心出版的第二年,是第二帝国,是晚清!我竟然在看一个这样的房子,这里面有多少孤魂野鬼住过?
回我的小城时,德铁又「准时地」取消+alternative的班次也「准时地」延误了。
2023.10.30 读Ocean Vuong的新小说,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这让我想起一个1.5代华人移民朋友,她一直在主流外媒工作。我打官司时,她曾采访我。前段时间在瑞典的一个新闻Fellowship上,我们重逢了,聊了很多文学类的话题,不再是采访者和受访者的关系。她离开美国后,一直在亚洲各种地方生活,印度、中国、泰国等等。我们有一个非常相反的人生轨迹,连读书都是。我是先读Rushdie,进入英文系后再读Jhumpa Lahiri。她则是相反。我喜欢她邮件发给我的一个她所写的短篇随笔。
我能理解到她使用英文为母语的优美和伤感,就好像看的这本书一样。这本美好的伤感的书。我们在这片大地上,曾短暂地绚烂过。
(结束。我没想到把所有这些很短的段落结合起来,竟然会有九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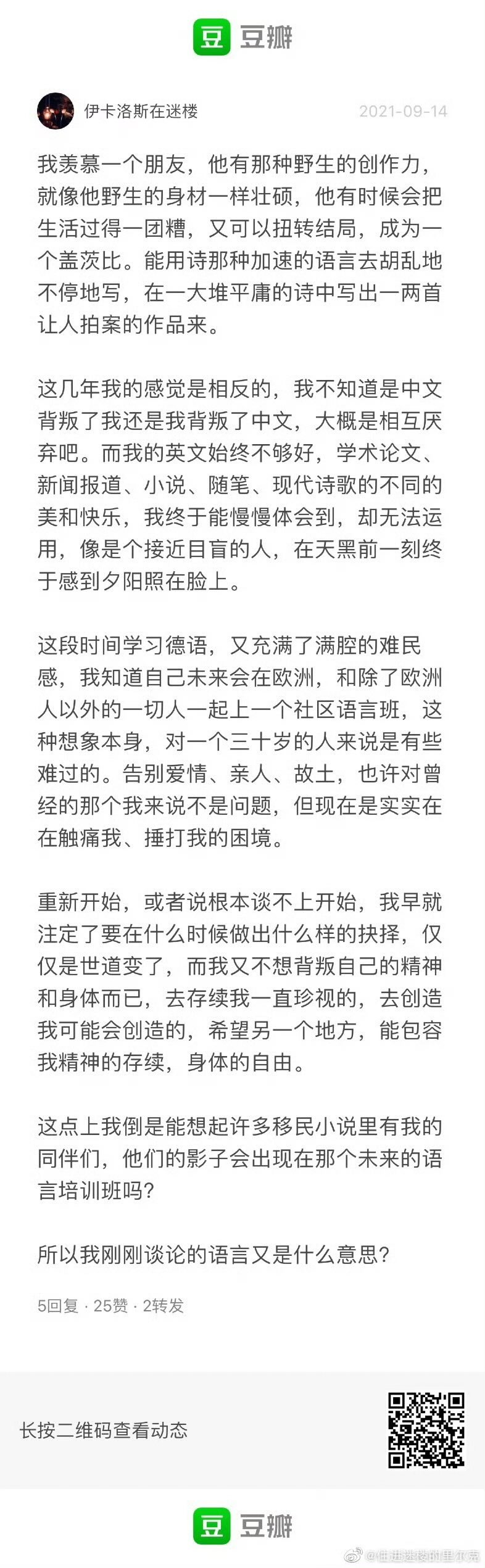
花了一些时间,分了两次终于读完,感觉就是三个词: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哈哈!
从微信公众号追到这里来,希望你多多写作表达!
我今天和朋友聊到你,我是你的超级粉丝。之前偶然读过你和杨一的访谈,听过你在不合时宜和三明治的对谈播客,非常喜欢你的表达!一直在追你的动向。我今天和朋友视频的时候,跟她介绍了你,她正在申请博士想要润出去,我们都对墙内环境开始深深的不安和渴望离开。我也跟她介绍了伊拉斯谟项目。
希望你能继续“漂泊着”,把我们心底的表达讲出来。某些程度上也是对墙内人莫大的鼓励~
写的真好, 我一直知道自己在移民的道路上是幸运的, 没花什么钱, 找工作顺利, 上班环境也不错, 交到了新朋友, 构建了新生活(但跟所在国又是很疏远的距离). 但说到底却也是被迫离开故土, 总归是丢下了一些. 这种失去就我个人来说不能说创伤和疼痛, 甚至放到少年时期, 这样的出走是梦想中的生活.
到了中年, 对归属感的需求渐强. 偶尔也会困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是基于族裔还是基于文化, 还是基于在哪国哪地生活的更久, 当然这些都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最后会落到非常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倒是挺期待有关于欧洲华裔移民的小说的, 觉得欧洲的历史感和复杂度和美国移民环境挺不一样的, 哈哈.